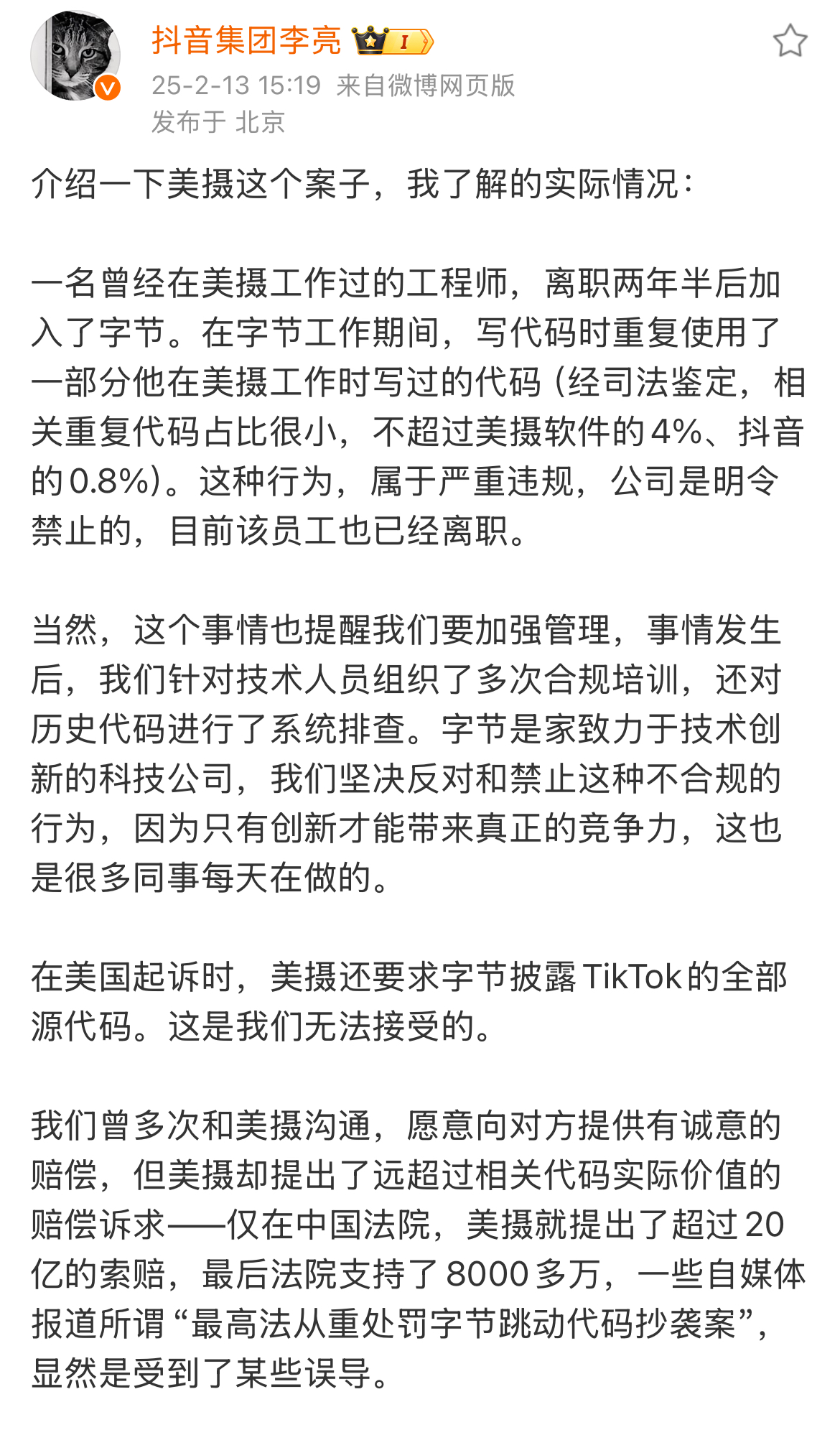这部《罪与罚》的序曲,让读者质疑关于犯罪和破案的一切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第一次看到这话,你觉得新鲜、好玩、有趣,就用到自己的口语里。你说,你一再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直到有一天,你会明白你自己正是这么做的——自己无路可走时跌倒并躺下。
160年前,圣彼得堡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一本新书。他那时身体康健,预期自己将在1864年初再次病倒,同时,他太太的结核病已有不容乐观的征兆,他哥哥米哈伊尔新办的杂志《真理》(次年改名《时代》),在发行了6个月后前景尚不明朗。他为《真理》向屠格涅夫征稿,并在信里告诉屠格涅夫说自己很快就要缺钱……他的新书以第一人称“我”开头: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
在这段自述中,“我”告诉读他的人,他知道自己满怀恶意,但说不清楚这恶意是向着谁而去,想要损害谁。他清楚自己不看病对医生是没有妨害的,妨害的只是自己的健康,但他仍然坚持出于恶意地不去看病。“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看上去多么眼熟。只是,你用轻松戏谑甚至显摆机灵的口气说着“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是用真实的、自虐的口气在诅咒他疼痛的肝脏。自虐,在俄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突出的倾向,因为俄国人很容易领悟到一个黑暗的事实,即个体在痛苦下的反抗是常常找不到对象的。正如卢梭所讲,社会不公源于体制而非个人,但体制和俄国广袤无边的大自然一样,冷漠无言、不会回应。为此,反抗才收缩为一个个人化的形象,他自虐,并使人惊悚地想起“谑”与“虐”之间其实没有区别。

“理性利己主义”辩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3年底开启了他真正成熟后的创作生涯,《地下室手记》是其中的第一次尝试。小说本身就写得艰难,在1864年4月2日的一封信里,陀氏告诉哥哥米哈伊尔,他已经近乎崩溃:“妻子真的快要死了。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我等待着她的死亡。”而他自己“大半个月都在生病”,只能在每天上午努力地写一阵子。陀氏对妻子很有爱意,他曾告诉屠格涅夫,那是他一生中所遇的“最纯洁、最高尚、最厚道”(爱用最高级形容词是俄语的一大特色)的女人。谁曾想,就在《地下室手记》终于完成并刊出后不到两个月,米哈伊尔也急病去世。他只留下300卢布,葬礼之后所剩无几,而寡嫂及孩子都得靠陀氏来照应。
这几个月的悲剧变故带来的刺激,无疑反映在了小说的调性之中,但是,“地下人”,这个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暴躁,阴郁,自视甚高却只能瘫在地上(为此他也被称为“俄国哈姆雷特”),朝着一群假想的观众发表宏论的40岁的下岗官吏,却产生于陀氏针对另一本书的辩难冲动。这本书就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作,出版时他本人尚在狱中,现在读它,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乌托邦味道很重的幻想作品,其销量和热度竟超过了到1863年为止的任何一本俄国小说,而且还得到了沙皇相关审查机构的出版准许。陀氏讨厌此书,固然有嫉妒它的畅销的因素在其中,但他也确实考虑去写一部更完善的小说,以抗衡《怎么办?》所传达的理念。
这种理念,我们如今称之为“理性利己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成,他提出,只要每个人都能贯彻理性利己主义的原则,俄国就能像英法等先进的西方国家一样,建立一个光辉的、人人得到满足的世界。当然,“只要……就……”的假设句式可以换成“只有……才……”的条件句式,免得看起来太幼稚,不过,“理性利己”的设定,看起来也不失有理,它断言,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争取利益,利己是出于理性也应该出于理性,众多这样的理性人集合起来,是可以形成一个好社会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故事的方式来给出一个“实例”,故事中的人因理性而健康,行动审慎有智,不乏热情。车氏把被屠格涅夫等人“抹黑”了的俄国一代新人扳到了一个正面的形象之内;屠格涅夫认定他们都是动机卑鄙的虚无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站到他们一边,说他们的激进将会有益于国家。而陀氏虽然与屠格涅夫很熟,却也不情愿只做一个专擅诽谤诋毁的保守分子。《地下室手记》深思熟虑地使用了第一人称,它驳难《怎么办?》里的白日梦的方式,是所谓的“现身说法”:你不是说今日的风气是理性、开明、未来可期吗?那你看看我,看看我这个满腹恶意的病人!
对“理性利己”的一番鄙夷,构成了小说中最核心也是最清晰的一段议论:
“什么是利益?你能准确无误地定义人的利益是什么吗?假如有些时候,人的利益不在于做有利可图的事,而在于做不利于自己的事呢?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有时,利己恰恰必然包括损己。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设定就要归于破产。”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1863年9月路过威斯巴登时,玩了一把轮盘赌,赌博的恶习就此上身。1871年4月28日,他从威斯巴登写给续弦之妻安妮亚的信,可谓一份忏悔录,他告诉妻子说,自己输光了她给的30个银马克,渴望她再寄一笔同等数额的钱来,并发誓说“今后我将考虑事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整夜幻想赌博”。他把自己输钱的经过写得丝丝入扣:如何掏出钱来,如何赢了一小笔,血如何上涌,如何梦见了亡父,如何在狼狈离开后奔向牧师那里却最终没去,而是回了家……并非使用什么“小说家笔法”,而是在用叙事来自疗,用口气过分的忏悔来书写一场“损己”的体验。赌博,这种人类社会中最独特的游戏,令陀氏在长达8年时间里深味自虐的感觉。
当然,落入赌场的赌徒也不失为“理行利己”之人,但他们在受挫后继续无法自拔,之后无论输赢,都是对自己的严重损耗。在让“地下人”谈论“人的利益”的时候,陀氏怎能不想到赌场的诱惑?他都可以预期今后的沉沦,就像预期下一场癫痫病发作就在不远一样。
他还有其他恶习,“洁身自好”是与他不沾边的。“地下人”对圣彼得堡热辣、拥挤的街道和下等夜总会充满感情,这些地方弥漫着一股由漫不经心、疏于管理的简陋、自暴自弃、冷酷无情乃至肮脏所交织而成的氛围。“地下人”在此间流连,关键是,他对自己“在此间流连”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小说里反复的自我解剖,一如他写信的风格:
“我羞愧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能感受到某种隐秘、反常、有点下流的快感;这快感就是,在某个最令人厌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往往强烈地意识到今天又做了件卑鄙的事情;而做过的事情又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挽回的,这时,心里便会暗自因这一点而对自己咬牙切齿,责骂自己,折磨自己,直到那痛苦最终转变成了某种可耻的、该诅咒的乐趣,最后,它竟变成了明显的真正的快感!”
“水晶宫”的幻影
耽于污浊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可是,“地下人”对他所鄙视的人——主要是那些迷恋西方进步思想的人,他们是进化论、科学至上、功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信徒——抱有显然强烈的优越感,以至于他能够基于自己的病痛、贫穷、卑微无名产生凌人的盛气。那些人心目中的圣殿,也是《怎么办?》企图打造的理想社会的缩影,正是1861年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的会馆,那个通体透明、辉煌靓丽的玻璃建筑“水晶宫”。西方人的雄心、智慧与成就都凝缩在此了,但《地下室手记》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和他那绝非吹毛求疵的怀疑:
“你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想法;你感觉,这里已经达成了某种成就,这里得胜了,奏凯了。你甚至开始隐约地害怕,害怕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必须接受这是终极真理,并自始至终保持情绪稳定?这一切是如此庄严、豪迈,满是得胜的气息,以至于你都喘不上气来”。
这建筑的志得意满的气息令他深感愤慨和不安,可是愤慨并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成为本雅明、昆德拉的先行者,从一种光灿灿的造物中看到“媚俗”。他传达的想法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一个过于如日中天的人造物,对个体人是很大的威胁,它的完美将导致它离丢脸不远。

只需要一把小锤,就能让“水晶宫”变成一个笑话。“地下人”倒不想亲自执锤,他是疲弱的,说的意愿远远大于做。他的锤子是言说:这座建筑所代表的一切——工业资本主义、科学理性,以及任何预测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型(包括今日的所谓“算法”)——都被他用言语反复锤击。“水晶宫”如此确信人们会喜欢它,仿佛掌握了人心所向,仿佛只要人类一看到它,就会明白它是所有人共同利益的汇聚点似的。围绕它的所有自负,都源于对它本来的样子故意视而不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蔑视、愤慨,底气都来自明白和承认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让我的肝疼得更厉害点吧!”
他奚落他的听众,然后道歉,再批评自己,接着又咄咄逼人,说着说着再次陷入崩溃,如此反复。他是如此矛盾,却乐此不疲地揭露自己,让人在他诚实的表演面前感到尴尬。一向狂傲的尼采都在《偶像的黄昏》里说,陀氏是他唯一能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索尔·贝娄则心服口服地把他的几部主要作品——《赫索格》《受害者》等——都归功于“地下人”的示范:个体在无法撼动强大的压迫性力量时,只能采取自我贬抑的做法,彬彬有礼地受虐。《赫索格》的第一句话,仿佛也出自“地下人”之口:“摩西·赫索格想,如果我失去理智,我也无所谓。”
管风琴的琴键
“地下人”嘲笑那种“算法自信”的话语集中在小说的第八节里。他说:假如有一天,人们真的能找到能测算人的愿望的“数学公式”,到那时,人肯定不会再有什么愿望了。因为愿望都被定下了,白纸黑字地写明白,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脱不了它的计算,就此,“地下人”说出了一个精巧的比喻:
“他还会立刻从一个人变成管风琴中的一根琴栓,或者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意愿,那还算什么人呢?这不是跟管风琴中的琴栓一样了吗?诸位高见?咱们来计算一下概率——这情形会不会发生呢?”
“管风琴的琴键”,这比喻真称得上“尖刻”,而非对人的诋毁。不难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如何看待现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广告技术以及各种民意测验,这类事物、学科、机构、活动的趣旨都在于预测人们的意愿:这可笑吗?把形形色色的人归为数目有限的一些偏好的体现者,这是否过于狂妄?
有一件事老陀当然是预见不到的:当某些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只要把人看做琴键,他们就真的会成为琴键,只要坚持把人看做被动的物体,他们就会成为那个任人摆布的样子。“地下人”说,人深不可测,是不可知的;人尤其应该拥有损己的权利,不能任由别人决定,到底什么是对他有利的。对这一点的坚持,将使人抵抗社会控制性的力量,但是,大量学科和技术都在为这种力量服务,企图使人的可预测性成为一种令每个人服从的事实。
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人们在谈到无止境地坚持时会提到他,在说到徒劳无益的消耗时也会引用他。对“原型人物”的理解和使用,各人可以依自己的心愿,没有一定的解读。“地下人”也是如此。当一场大疫降临,被困在家中的苦闷的人,有些能从“地下人”的讲述中找到安慰,有些则相反,认为他是在鼓励逆来顺受,无所作为,是一个反面的榜样。这种模糊暧昧,可以解释在《地下室手记》1864年问世后的遇冷:老陀想用此书来针对《怎么办?》,可是读者们难以真正领会他的意思。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场滔滔不绝的宣讲,没有人会忍受这个人在自己家里待上半个小时以上,幸好他只存留在书页中,他的清醒的恶毒、矛盾的自说自话才得以被欣赏。到第二部分,“地下人”开始讲个人经历:他回到了16年前,那时他24岁。他曾一直对一名军官心怀不满,因为这名军官在酒馆里随手将他抱起来,挪到另一个地方,事情发生时都很和谐,他心里却恨得无以复加。同年,他受邀参加一个老同学办的晚宴,在场的毛头小子都招他的怨恨,他们都粗鲁得不值一提,可他依然渴望得到他们的尊重。结果,晚宴上的他出尽洋相,最终他在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寂寞的风尘女,两人聊了好几个小时。女孩聪明、正派,却陷入了绝境,他对她屈尊俯就,说教连连,心生恐惧……
车尔尼雪夫斯基考虑的是“怎么办?”老陀却一直探讨“为什么?”: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地下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他都设法解释,却又无法解释,只是围绕着解释的对象堆积起了痛苦的陈述,在其中,一个不能被预测的个体显示出了存在和被书写的价值。两年以后,老陀的新作《罪与罚》,将会把他眼里的人的复杂性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更具可读性的高度,谋杀犯拉斯柯尔尼科夫,成为文学经典里一个经典的形象,一个复杂人性的精美化身。他逃不掉处罚,可读者却被作者拖进了一场洪流之中,去质疑围绕犯罪和破案的一切——从制度安排到道德判断。人是不可预测的,也不该被预测,作为《罪与罚》的“序曲”,《地下室手记》先期讲出了这一点。

《地下室手记》
[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6月版
广东印发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支持企业上市和挂牌融资
对准备上市、挂牌企业因改制、重组、并购而涉及的土地手续完善、税费补缴、产权过户等事项,建立健全绿色通道、限时办结等制度,加强政策指导和服务,协助企业妥善处理。0000机构今日买入这15股,抛售中文传媒1.81亿元丨龙虎榜
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的股票分别是润本股份、五方光电、安培龙,净买入金额分别是3663万元、2920万元、2118万元。盘后数据显示,12月25日龙虎榜中,共28只个股出现了机构的身影,有15只股票呈现机构净买入,13只股票呈现机构净卖出。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的股票分别是润本股份、五方光电、安培龙,净买入金额分别是3663万元、2920万元、2118万元。锤子财富2023-12-25 17:55:310000职工医保费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国家医保局辟谣
国家医保局表示,网上流传的“取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相关文章内容和截图完全是造谣,我们保留追究相关造谣者责任的权利。10月27日,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一篇名为《职工注意!2024年起,职工医保缴费将彻底改变》的文章和相关截图在部分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网上传播。经核实,文章中“职工医保费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个人将不再有自己的医保账户”等相关内容纯属造谣。0005国务院批复同意将福建省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务院发布批复,同意将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发布批复,同意将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文如下:国务院关于同意将福建省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国函〔2023〕10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你省关于申报莆田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0000“商汤日日新”大模型体系全面升级,飞速迭代赋能百业日日生新
锤子财富2023-07-08 09:27: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