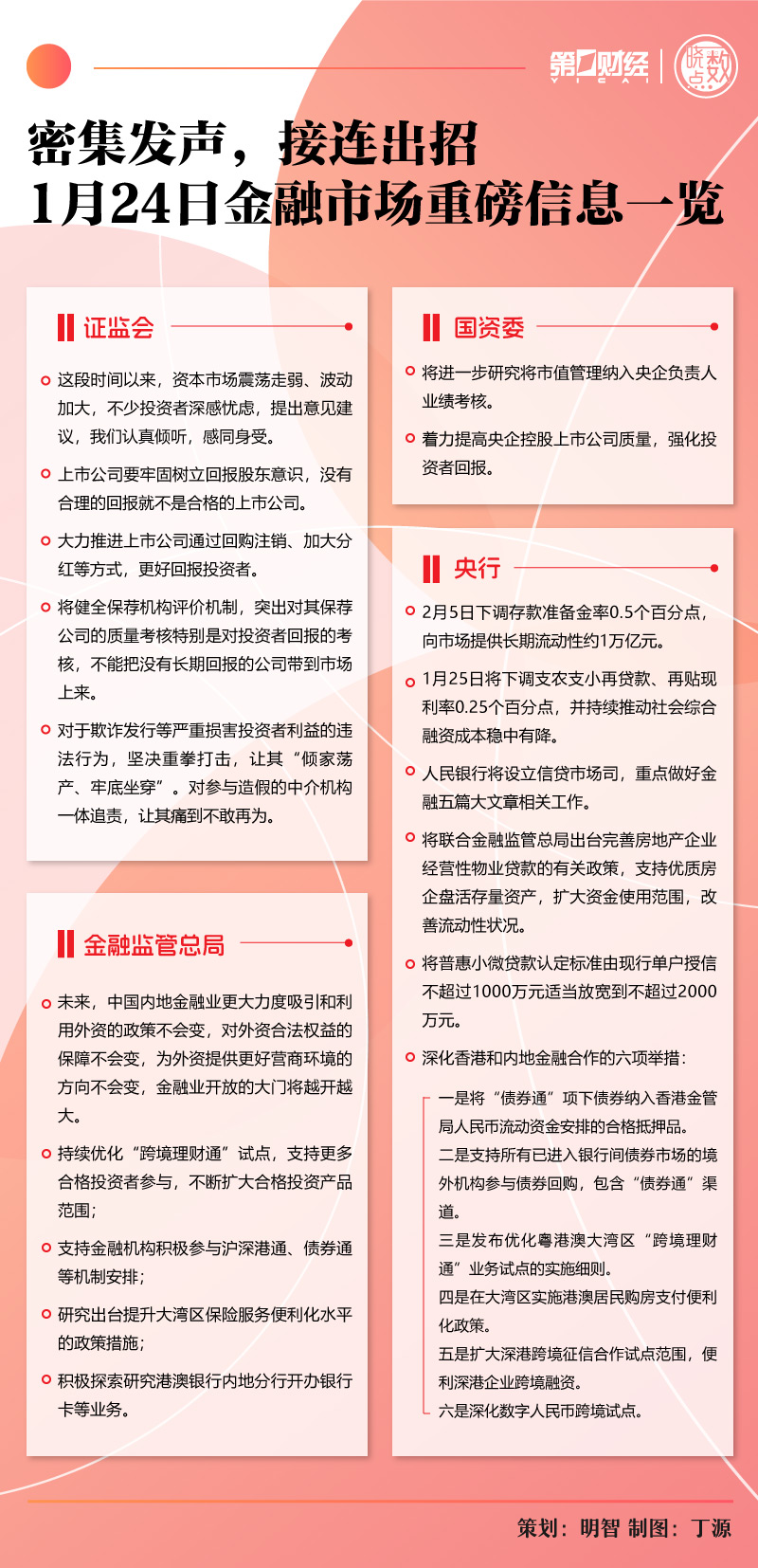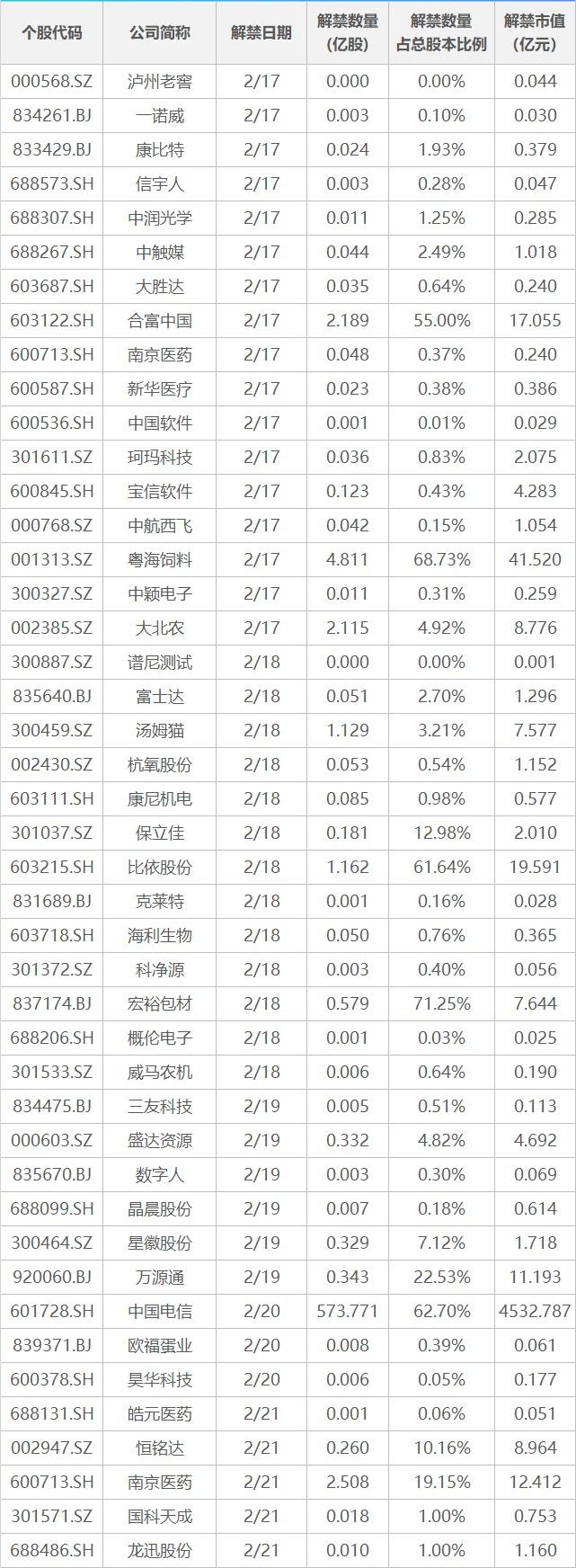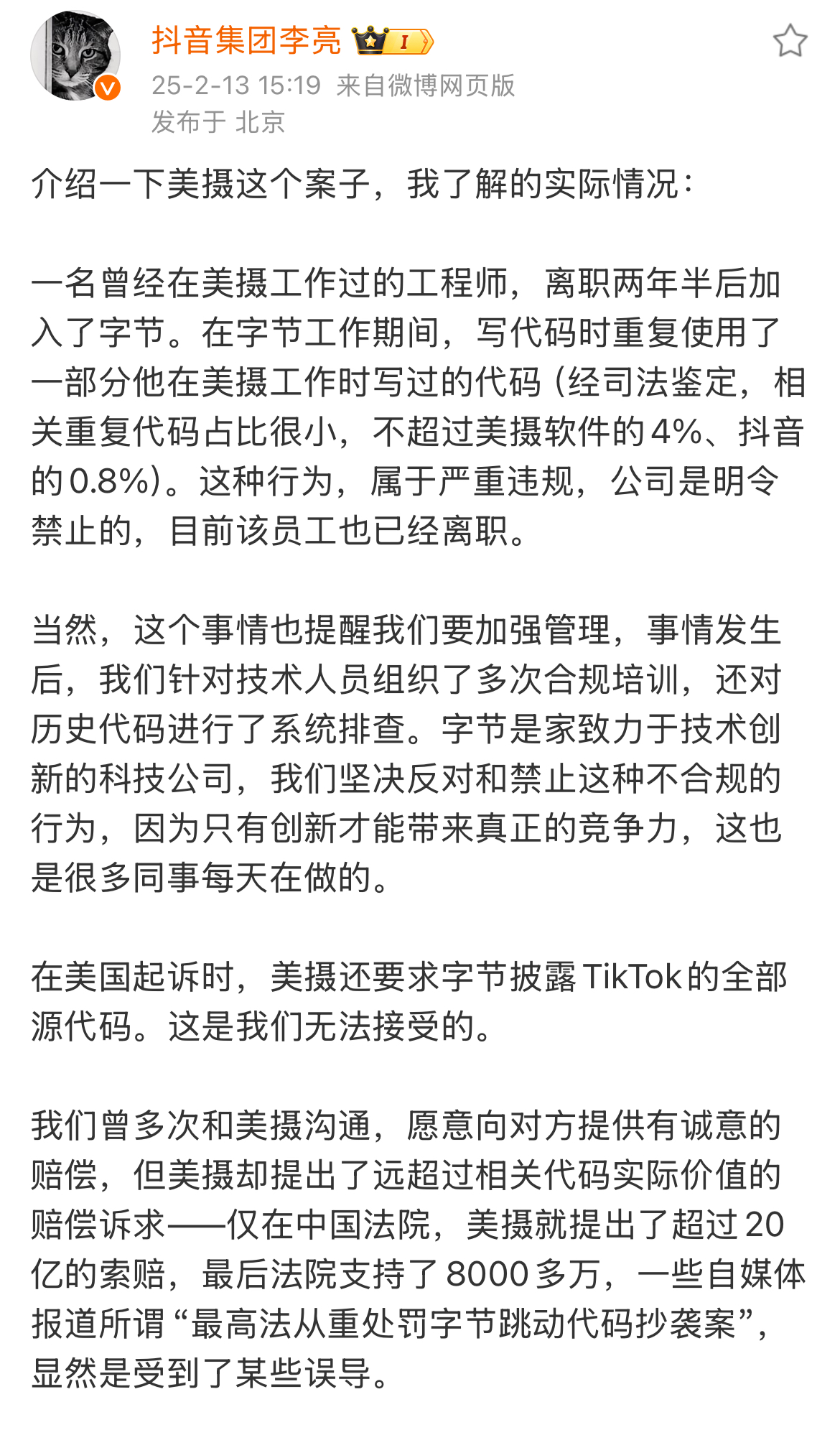西方艺术家百年前曾会聚巴黎,共同学习东方艺术
在西岸美术馆的展厅,有两幅作品并置而立。乍一看,它们颇有相似之处。右边的书法立轴上,是清代傅山笔走游龙的草书。左边的画框里,同样是宛若天书的墨水勾画,阅读展签可知,这是1959年法国诗人、画家亨利·米肖的作品。
在20世纪,有这么一群艺术家,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黎,他们对西方启蒙概念产生了质疑,对东方哲学艺术充满了向往。从中国书画到东方禅学,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并将对其理解汇入艺术创作。这些艺术探索起初是拙稚的、异想天开的,但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最终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重要支流。
4月29日至9月24日在西岸美术馆举行的展览“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方”,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讲述超现实主义的故事,也让观众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当代艺术,以及中国传统书画。

遥望东方
“和艾略特的《荒原》一样,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的诗意化产物。”本次展览策展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迪迪埃•奥廷格表示,“这场艺术运动的大部分中心人物都有参战的经历,遭遇过对他们而言最恐怖的情况。”
一战带来的集体性创伤,让欧洲人陷入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知识界甚而开始怀疑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于1918年至1922年发表的《西方世界的没落》畅销一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在对战争创伤进行分析后做出了文明中的“萎靡”的诊断。
超现实主义的领军者安德烈•布勒东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在熟悉其诊疗方式后,他决定拿自己做实验,“展开一种尽可能快的独白……思想未必能快过语言,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一支挥扬疾书的羽毛笔。”
布勒东和安德烈·马松等艺术家发展出一种名为“自动主义”的创作方式,任由“画笔在纸上飞驰”,勾勒出一种超越意识的诗意,他们很快发现,这与抽象而神秘的东方艺术冥冥相关。

乔治·杜图伊特在1936年的《中国的神秘性与现代绘画》中写道,“正是中国人的祖先最早发现和探索了想象力的未知疆域,他们一定不是为了在那儿划出固定界线,而是为了在广泛扩展其边界的同时,展现其丰富的内涵。”
事实上,当时的艺术家了解东方的路径是非常局限的。马松回忆说:“如果我记得没错,在1925年左右,一个身处巴黎的年轻画家鲜少能接触到远东水墨画。在无法见到原作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查阅翻印了大量相关作品的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专著,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奥廷格同时指出,此时超现实主义者所谓的“东方”也是一个地理位置不甚明确的概念,它同时涵盖了俄罗斯和其纷争不断的边境疆域,以及远东的中国、日本及印度。
直到二次大战,马松流亡美国,他对东方艺术的认识才得到进一步开拓。“幸亏这流放生活,我才能在波士顿大开眼界。这座城市的美术馆足以为它那最丰富的中国艺术大师收藏而感到骄傲——尤其是那些宋朝的作品。人们可以在那些中国和日本寺庙的收藏之外,慢慢欣赏这些作品。”他开始“像禅宗的僧人那样任意喷洒墨汁”,他留白、书写,他模仿石涛和雪舟的方式,尝试并着迷于“没骨”画法。

展览开篇的另一位重要艺术家是胡安·米罗。1921年3月,米罗搬到巴黎布罗梅街45号的工作室,并在此结识了邻居马松。当马松受到书法的启发,沉醉于自发、极速的肢体动作,米罗则对东方绘画中的抽象性与诗意感到心驰神往。
他开始把字母和词语运用到构图当中,在当时的艺术评论家杜图伊特看来,这就像是“远东的那些卓越的艺术爱好者会在大师的画卷上题写他们的诗句,有的最后甚至会把整幅画面都铺满”。
米罗在“星座”系列中探索着图像和词语之间的界限,22件作品占据了一个完整的展厅,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象形符号和表意符号。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夜莺的夜半歌声与晨间的雨》《女人被鸟儿的飞翔所环绕》《第13日,天梯擦过苍穹》……在该系列作品的对面,是他另一件长而扁的画作,仿佛是中国画中的长卷。
在1973年米罗生日之际,马松回忆起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将绘画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梦想:“当时的胡安和我都认为,广义上的诗歌是十分重要的。成为‘诗人画家’曾是我们的目标,也是这一点把我们和前辈画家们区别开来。”

中西切磋
1952年12月,安德烈·布勒东与评论家夏尔乐•埃斯蒂安一起,为位于巴黎普雷奧克莱街11号的“封印星”画廊揭幕。这里将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遥望东方的新基地,画廊先后推出的让•德戈特克斯、西蒙•韩泰、朱迪特·雷格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出现在本次展览中。
布勒东曾将德戈特克斯充满禁欲主义和冥想的作品比作禅宗绘画,并在策展文章中夸赞其作品“气韵生动”,“德戈特克斯的艺术创作同时再现了中国人所说的‘气韵’(画家一落笔即表现出的内在灵性)和‘生动’(富于生气和活力的运笔)。 ”艺术家本人也赞同这种说法,他对《箭术与禅心》以及铃木大拙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读,创作出《须弥山》《书道》《剑道》《风生》等一系列富有禅意的作品。

匈牙利艺术家西蒙·韩泰与朱迪特·雷格尔先后来到巴黎,并不约而同地被超现实主义中的东方内涵所吸引。雷格尔通过女性的敏锐直觉把握东方艺术的精髓,她在展览中的多幅作品给观众带来充满禅意的冥思。而西蒙·韩泰则从超现实主义逐渐转向了行动绘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杰克逊·波洛克的影子,后者作为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很快成为战后西方艺术的领军人物。


中国古人诗画同源的境界,在20世纪巴黎的艺术家诗人团体得到了遥远的共鸣,他们将符号和书写联系在一起进行视觉艺术的创作。克里斯蒂安•多特雷蒙发明了语素文字,他用在纸上自由地绘制诗歌,起先用钢笔、粉彩,而后使用墨汁,连缀在一起的字母组成的弧线游走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组成一幅幅象形的图画。冥冥之中,这幅画面与展厅开始处傅山的书法形成了对照关系。

本次展览,上海博物馆特意从馆藏中挑选了多件书画,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进行对话。上博书画部主任凌厉中表示,“在现场,有观众问我,某件书法写的什么内容?我的建议是,你不需要知道。书法的线条就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你不用被里面的内容干扰。”
二战以后,中西艺术交流开始变得更加密切。1956年夏天,张大千来到巴黎,在塞努奇博物馆举办个人收藏展,又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个人艺术展。“那些巨幅画作足以让一个法国人感到震惊,”马松赞叹道,这让他清晰意识到“自己使用墨汁的方法是多么简易和基础”。
此时,出于对学习欧洲艺术传统的渴望,一批中国艺术家来到了巴黎,这其中包括1948年抵达的赵无极、1952年抵达的丁雄泉、1955年抵达的朱德群。本次展览另一位策展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收藏部策展人玛丽·萨雷提出,而当这批艺术家颇费苦功地试图在创作中摆脱最后一丝“中式”痕迹,融入西方艺术圈,他们也无意间为欧洲的同行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
展览最后,亨利·米肖的作品与赵无极的作品面对面陈列,二人于1950年首次会面,并成为了一生的挚友。米肖一直对亚洲充满热情,他多次前往亚洲旅行,并将其经历记录在1933年出版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一书中,他称中国画“深入他的内心” ,激发他创作了在白纸上点缀律动的黑色符号的一系列水墨画。赵无极在1948年来到巴黎学习绘画的时候,曾试图努力忘记自己所受的传统书画教育,然而,中国画的基本原理仍然存在于它的大尺寸抽象画中:自然奇观、留白结构、缺少透视,乃至象征的涌现。他在米肖的画作中看到了与中国书画的联系,并慷慨地与之分享探讨。当赵无极回归水墨画时,米肖也欢欣鼓舞:“真高兴啊!他找到了世代相传的智慧!”

文化误译
西岸美术馆的展厅布置得有点像是中国的园林,并非传统的单程线性,而是更加曲径通幽、迂回辗转。展厅里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而今已汇入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究其本源,又与中国传统书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自上海博物馆、穿插陈列于展厅中的龚贤、董其昌、八大山人的书画时刻提醒着这一点。漫步其中的观众,不时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些分别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创作,它们到底像,还是不像?
在开幕式之后的论坛上,有观众提出了这个问题:超现实主义的肇始是注重无意识表达,但是中国的文人画,看似抽象写意,实际上根植于深厚传统,本身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艺术家的面向东方文化的冥思和灵光乍现,会不会只是一种误读?
对此,凌厉中认为,中国传统书画确实是有传承关系,“例如董其昌,以古人为师,但他也有一句话,以天地为师,这两个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对于艺术的理解。”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艺术家从未忽视对宇宙、对自然的感悟,并认为笔墨是有生命的,从线条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质,这些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奥廷格也以乔治·杜图伊特的《中国的神秘性与现代绘画》为例,阐释了当时欧洲人对于中国艺术的理解,书中提出中国绘画不是形而是诗的王国,中国艺术家善于把自己融入宇宙能量,同时通过绘画的迅速性,把天地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展览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画作。”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误会,有时恰恰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蔡涛曾经举办过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展览,1930年代,决澜社等艺术团体就曾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他介绍说,超现实主义虽然源于欧洲的一战创伤,但它传到日本的时候,恰逢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人将其中的梦幻和诗意解读成一种乐观态度,而后,因为时局的变化,一些日本艺术家又将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手段。“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许开始是从表面上学习一些创新,同时也在将其内化为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
奥廷格也认为,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征就是跨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核心是对话,艺术家可以从其他传统、其他历史中学习。”他也注意到,当亚洲艺术家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来到巴黎,他们接触到的已经不是最初那种抽象的、书法的、自动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加泰罗尼亚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比他们早一步来到巴黎,他以写实的手法描绘梦境在当时大为流行。“亚洲艺术家在巴黎遇到的这种绘画,并不是超现实主义美学的第一个版本,如果他们早一步抵达,本可以发现,它与自己的传统有如此多的相似……”
吉利德、艾伯维相继折戟后 国内创新药企能否撑起CD47研发
血液毒性和疗效不佳是CD47药物研发的两大“拦路虎”。目前,制药企业都在探索可能具有疗效前景的适应证。作为免疫治疗领域的热门靶点之一,CD47近年来吸引了包括吉利德科学、辉瑞和艾伯维等制药商的关注,巨头们在CD47药物的开发上掷以重金,通过收购或授权引进的方式,押注下一个重磅炸弹式药物。0000从AI开创者到“末日预言者”,“人工智能教父”离开谷歌
辛顿在Twitter上澄清,离开谷歌并不是为了批评谷歌。“实际上,我离开是为了谈论人工智能的危险,而不用去考虑这对谷歌有何影响。”他写道,“谷歌的行为非常负责任。”在业内有“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他上周已经离开谷歌。辛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帮助谷歌开发AI技术,但他现在成为了人工智能最新的“末日预言者”。锤子财富2023-05-02 17:39:210000辽宁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王英接受审查调查
曾任东北制药集团副总经理,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沈阳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辽宁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王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英简历王英,男,汉族,1959年1月出生,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0000